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时,邱大川照旧在店里捣鼓他那部电脑。
那是三月底的一天,远在浙江打工的母亲急需买药,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药店。由于不识字,又抓不到人问路,她想让儿子帮帮她。
这是许多进城务工的老人常遇到的窘况——看不懂地图,只好请亲友远程指路。又是电话,又是视频,两母子费好大劲才找到不过200米外的一家药店。挂断电话,邱大川决定为母亲这样的老年人开发一个小程序,专门用来认路。
邱大川今年36岁,九年前从北京返乡,在老家四川南充下面的小镇开了一家建材铺。从大城市“急流勇退”后,生活节奏慢下来,他在看店的间隙自学起了代码。根据自己对小镇生活的观察,这位“野生程序员”还开发过文字信息转语音、山寨品牌识别、手机练打字等小程序。
作为一个农村孩子,他看过太多中老年人为了孩子,坚持留在城里,直到干不动了才回乡。现在生活的小镇老龄化程度也极高,总有老人走进店里求助,时常让他思考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
四月初,这个叫“附近搜搜”的小程序上线后,母亲的使用体验很不错。邱大川想解决更多父母的认路问题,把二维码发到了豆瓣“适老化改造促进会”小组,获得了热烈反馈。帖子发布当天,小程序的使用量冲到了四五千。
当衰老不可避且无可逆,作为未来的老人,应该从时代的缝隙里拉他们一把。通过邱大川惊人的洞察力和行动力,我们试图安慰自己,只要有人愿意作出改变,变老就不是那么可怕。
一
“适老化改造促进会”
母亲的那次电话,是邱大川关注“数字鸿沟”的起点。她打工的地方周围都是工地,因为疫情停工,到处问不到人。线上地图更是难用,别说不识字,即便打开关怀版用语音搜索,得到的也只是字体放大版,使用方式没有变得更简单。地图上红色的指针图标挤到一起,“我”的位置模糊不清,必须放大页面、来回拖动,这对年轻人都不是一件易事。
母亲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千里之外的儿子。她把微信定位发过去,告知想去的地方。儿子在这边搜索到路线,母子俩再通过语音导航。远程指路难在母亲不知道方位,也不认识路牌。邱大川要不断确认她周围的建筑物,来锚定她面朝的方向,再引导她左转或右拐。
这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刺痛时刻。当人们逐渐不再依赖问路,只留下他们在路面上茫然无措。年轻人或许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:走在街头,不时会碰到一两个求助的问路,或是对智能手机的咨询。这些客气的目光里,总流露出一丝胆怯。
于是从一开始,邱大川就确定了小程序的设计思路:用法越简单越好,功能越单纯越好。
他筛选出老年人常去的场所,在页面整整齐齐码好,用按键代替自定义搜索,实现了“附近”功能的文字化。点击药店后,就会弹出附近的药店列表,自动按距离远近排序,店名、距离、地址清清楚楚写上。旁边配有橘黄色的小话筒,点击即可拨通店家电话。

“附近搜搜”小程序页面。
邱大川构思的使用场景是这样的:母亲要买一包洗衣粉,得提前打电话问问小卖部有没有。如果不方便出去,还能请老板跑腿一趟。假如要请客,她还可以打电话到某家饭店,那里煮的鱼好吃,让老板先煮上一锅。
对年轻人而言,这些早就集成在盒马、美团等App里的功能,只消动动手指就能实现。但对于老年人,特别是在互联网尚未辐射到的农村,这些需求还要费心劳力地自己上门。
母亲不认字,邱大川要让小程序里出现的所有文字都发出声音。他在每则文字旁都配上小喇叭,从功能按键到搜索结果,都可以点击朗读。
和大多数关怀App一样,小程序支持语音搜索。在这个基础上,邱大川还做了一个“请别人帮我找”功能。考虑到有部分老年人,对操作应用或手机有天生的畏惧,生怕哪里点错了。所以即便程序做得再简单,也不如亲友的帮助。这个功能可以把使用者的定位发给其他人,对方打开后,能够直接在使用者的定位上搜索附近场所。
四月份,小程序正式上线。母亲分享给身边年龄较大的好友,都说挺好用。邱大川想解决更多人的认路问题,把二维码发到了豆瓣“适老化改造促进会”小组,这里聚集了2万多个“未来的老人”。
反响比想象中要好。邱大川看完了200多条评论,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加入导航功能。这是他一直有的想法,却在实操中遇到困难。具体而言,是老年人很难听懂现有的语音导航指令。
比如,要找的药店就在马路斜对面巷子里。导航可能会让人先沿中关村北大街走200米,紧接着过马路,掉头往南走80米,然后进入海淀路,再告知目的地在右手边。如果向路人询问,就是一句话的事,导航反而把事情变复杂了。对于一个刚到陌生城市的老年人,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,东南西北都是不能理解的。
简单来说,给老年人的指令,需要在精确的基础上,多加一些人性化的判定,把指令集成更容易理解的话。从技术来讲,实现导航功能并不难,但他还在研究如何让老年人更容易听懂。
还有网友提议加入方言模式,或者把语音输入文字替换成语音发出指令。前者难度不大,邱大川记得讯飞就有接口。但他更想实现在老年人打开程序后,由AI助手询问用户来自哪里,并在设置方言后给出搜索指引。
邱大川的更新工作做得很慢很细,他希望每一次更新都能够真的解决问题。
二
与社会逐渐脱节的无力感
邱大川母亲生于1965年,今年57岁。年纪不算老,但那一辈儿女多,五兄弟姊妹中只有一个弟弟读书成才了,其他姐姐都没怎么读书。
不识字是母亲心里的疙瘩。以前在县城饭店上班时,同样从擦桌子收拾碗起步,别人熟悉之后能给客人开单,她操作不了。母亲干脆不干了,她内心抵触这种因不识字遭到的区别对待。
女强人一样的人,因为不识字,做起事来总束手束脚。邱大川的父亲在他11岁那年病倒了,母亲为了儿子的学费,选择独自去北京打工。几年后,父亲还是没能逃脱病魔,母亲也在异地待了十多年。她逐渐爱上北方的馒头,做得一手好炸酱面,有时还蹦出一句带京腔的川普。七年前,邱大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,母亲才回来帮忙带小孩。在家的时间久了,她甚至有点想念北京。

邱大川和女儿。
去年,母亲又离家到浙江嘉兴打工。她还是不愿意花孩子的钱,只要能工作,就想出去挣一点。另一方面原因,也希望用繁忙的生活抵过孤独感的侵蚀。父亲离开后,母亲缺乏安全感,变得容易多愁善感。邱大川作为独生子,几乎每天都要和母亲视频。加上社会走得太快,没上过学的老年人要适应,精神压力很大,她慢慢感觉与社会脱节。
包括大家在家族群里聊天的时候,她看不懂,也回复不了。虽然母亲不发言,但邱大川能感受到她的自卑,为此还开发过一个微信“外挂”。只要把文字信息转发给一个机器人账号,那个账号就能自动回一段朗读文字的语音。直到今年4月,微信关怀模式推出点读文字的功能,这个外挂才正式“退出江湖”。
后来用上微信支付,母亲又开始纠结100和1000的区别。在她的世界里,字面的数字还是很模糊的概念。她只能死记硬背100后面是两个零,1000后面是三个零。长此以往难免有纰漏,因此母亲从来不会在微信零钱包里放超过千元。
差不多在那个时候,很多以往唾手可得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。一个电视机配两到三个机顶盒,起码两个遥控器,几十个按键彻底把她难住。母亲熟悉的是那种12个频道的黑白电视,拧开开关,只有频道和音量两个按钮。现在她连打开电视都做不到——一进去就是广告,再就是各种App更新的弹窗提示,等进入网络电视的页面,还要切换成直播。
没有别的娱乐,她每天刷抖音快手,一个接一个看视频。母亲喜欢抖音极速版、快手极速版,刷视频有钱领,几天有几毛钱。买东西喜欢拼多多,总说官方又发钱了,一看只发了几分钱。平时去银行办业务,可能连名字都是勉强画出来。那么多砍价的操作,母亲却能把所有步骤记在脑子里,还乐在其中。
比起大多老年人,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母亲,生活的不便程度没有那么高。但更多人面对的数字鸿沟,宽到无法跨越。邱大川在疫情期间,亲眼目睹健康码行程码给老年人出行造成的困扰。他们的手机可能还是功能机,或者根本不会弄。在医院门口,他就看见过因为没有手机,无法进去看病的老人。
邱大川很心疼,觉得必须要改变一下。
三
不玩游戏的野生程序员
写程序是在五年前开始的爱好。邱大川那时从北京回到老家,生活节奏慢下来,不自觉想学点东西。他不喜欢打牌玩游戏,看店无聊之余买了本教材自学编程。一整本厚厚的书,不到一下午就能啃完。他对着书上的代码操作,理解运行逻辑,看多了就开始上手做东西。
选择做微信小程序,主要因为技术成本低。不像做App,要学习苹果安卓两套语言,上线也得缴费。个人小程序上线免费,地图数据库、语音搜索这些功能,各个平台都有接口。
除了认路的,邱大川还开发过几个小程序练手,其中一个用于商标识别。建材店开起来后,他发现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,老家的房子装修都是老年人在操心,他们中许多人无法分辨山寨产品。为了突出自己卖的东西正规,他才做了这个程序——只要拿手机对商标拍照,就能识别出品牌。他把小程序展示给每个来店的客人,用的人不多,他也无所谓,做出来就开心。
认路小程序发到豆瓣之后,流量经历了一轮暴涨,邱大川也想过要不要商业化。比如挂上广告,放一些老年人爱看的视频,黄梅戏或者川剧。后来想想还是算了,这么做显然违背了他的初心。
他是一个极其不愿意把事情搞复杂的人。喜欢做程序的原因,也是因为技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他没有改变社会这样远大的梦想,现阶段最大的关心事,是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技术补贴一点收入。用他的话来讲,就是做一系列“赚钱机器人”。如果在这基础上,还能稍微帮助到别人,就已经很好了。

邱大川在店里工作。
邱大川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程序员。在他心里,程序员是很酷的。这个世界发展得如此之快,很大程度是程序员的功劳。但他更享受开发的过程,没那么看重结果。没活干就在店里写写代码,有活的时候也到装修工地上去。
被称为“野生程序员”,他还挺喜欢的。用他的话讲,正体现了他“不务正业”的性格。本来应该好好经营店铺,却着迷于写程序。身边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会写,过路的人看见他整天在店里打电脑,都以为他在玩游戏。
和正经程序员相比,邱大川的生活环境反而赋予他独特的观察视角。他善于挖掘一些细微的需求,并且有很强动力去解决实际问题。这些观察都体现在他对小程序的设计中,借助他的眼睛,我们得以窥见小镇生活的一角。
他掰着指头数自己的研究,其中一个是苹果产品序列号的查询服务。小镇上有很多卖二手的手机店,激活时间、保修期、维修记录等都是收手机时的重要参考值,又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城里的苹果专卖店去查。百度指数显示,每天都有四五千人为此在网上搜索。
还有一款练打字小程序,专门针对没有学过电脑的用户。因为一位朋友当上村官,有电子办公的需求,却不会用电脑。他们所在县是近两年才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,这位朋友30多岁,一直没用过电脑。邱大川才发现,很多乡村干部甚至是老师,都有练打字的需求。
四
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
自从2013年回到家乡,邱大川感觉这里的时间过得特别慢。在互联网强势占领城市各个角落时,农村的社交、生活方式大多固守着以前的步伐。
整个镇两万多人,却很难找到一张青壮年面孔。当地劳动力在90年代大量涌出打工,搞建筑或者进厂。手停脚停,总要等干不动了才回来。剩在镇上的,除了老人就是学生。
在老家挣钱太困难,没有年轻人,就缺少重要的消费力。像邱大川这样在镇上做生意的,几乎很难突破月销售额15万元的免税额度。他所在装修行业,夏季更是纯粹的淡季。农村装修房子,大都在上半年。从广东、浙江挣来的钱,过年期间哗啦啦投进房子里。
从回来到现在,他感觉镇上的人一直在做一件事——盖房子,盖更好的房子。县城一套房才六七十万,在农村花两三百万建房的人却不在少数。特别是老年人,他们赚钱只希望孩子过得好,然后盖一栋好房子。

邱大川看着老家豪华的洋房,反思在北京住的西北望小平房简直不是人能呆的。
留在镇上的大多是老年人,房子装修自然都是老年人在操心,邱大川也最常和他们打交道。五个客人里,就有一个要现金支付,他们对电子支付还没有完全信赖。现在镇上开农村公交的司机,每天都要数一大把一块两块。
他的店开在比较繁华的地方,不时就有老人进来求助。比如,常有人问水气电费这种生活用费怎么缴。通常年轻人过年回家都会买够一年份,但总有不够用的时候。老人们攥着一大把零钱,到处问营业厅在哪里。
还有老人进店就说手机坏了,邱大川拿来一看,其实就是内存满了,一打开就闪退。他很奇怪,自己的手机从不会这样。但老年人总能刷出奇怪的销售广告,装上乱七八糟的应用,甚至有暴露信息的风险。
手机“修”多了,他就发现很多极速版App里集成了大量这类广告。在微信搜索老人或老年人,也会发现大量雷同的小程序,点进去就是各种广告或视频。为此,他还向腾讯投诉过,得到的反馈是操作本身没有违规,只是他们做的东西太烂了。
碰到过最离谱的事,是一次在房子工地上干活的时候,旁边监工的房东老人的手机来了电话,竟然要观看15秒的广告才能点击接听。这些广告的无孔不入,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
不刷手机视频,老年人也没有其他选择。邱大川记得,以前镇上甚至农村有露天电影、露天戏台,都是消遣的好去处。街角补锅补鞋的老头就像吸铁石,总会吸引一堆老年人坐着聊天。现在不仅补锅补鞋的没有了,修自行车的也没有了,搭个凳子在桥头给老年人理发的也没有了。手机玩不转,电视看不懂,属于他们的公共休闲空间消失殆尽。
所以邱大川很难谴责老年人的“网瘾”。对他们来讲,视频软件可能是唯一能够对话的东西。毕竟在算法的处理下,用户标签细分到每一种方言。线下的世界是孤独的,线上的世界反而是热闹的。

邱大川所在的小镇。
对于未来,邱大川想要在现有小程序的基础上,升级成周边生活服务集结的平台。把他观察到的,老年人交水气电费、找装修工人这些需求放到同一个入口,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地“一站式”处理事情。
当然这个想法能否落地还无法确定,他不清楚需要什么资质,也不清楚这个接口谁能提供。有的时候,他也会琢磨,这不是个人能带动的,而是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。毕竟科技不一定能为老年人所理解,但只要花心思,足以方便他们使用。
他现在能做的,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劝所有来店的客人,在马桶旁边装一个扶手,让老年人坐下或起身时能够扶着。淋浴间也要装一个高度在一米五左右的扶手,老人洗累了可以抓住扶手休息一下。顶多10多块钱的成本,对老人而言却是非常大的便利。
采写:南都记者黄慧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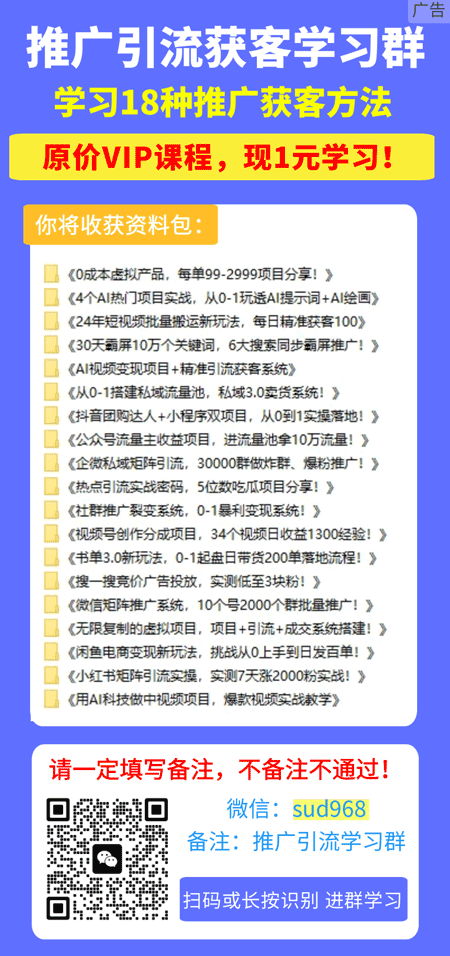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vsaren.org/26720.html
